张老汉在街角的大树下蹲了一天了。
中午,他啃了一个从家里带出来的馒头,天快黑了,他觉得肚子空空的。一天了,一个馒头也顶不下来。他回身摸了摸自行车后竹筐里的布袋,里面还装一个馒头。馒头有点干,张老汉的门牙去年掉了一颗,少一颗牙,馒头就啃得很辛苦。张老汉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馒头,额头上的青筯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条条暴起,显出非常复杂的图案。他想喝口水顺顺,拿起装水的矿泉水瓶,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。他摇了摇头,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把水瓶丢回自行车后的筐子里。水瓶在竹篾编的筐子里翻了个跟头,一声不响地躺到了竹筐底的一片菜叶子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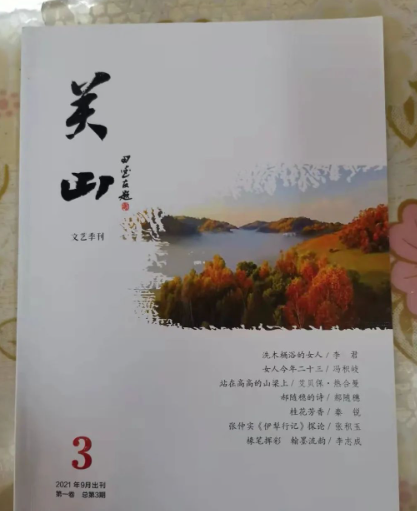
还剩下三把菠菜一直没人买。看看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,张老汉有些着急了。早上出门时,还生机勃勃,叶子劲挺的菠菜,现在有些蔫头耷拉的,像张老汉一样垂头丧气。只是菜叶子还是碧绿的,这种碧绿的颜色,给了张老汉信心,应该能卖掉!张老汉想。
张老汉抬头看看天边最后一缕亮光,又靠着树圪蹴了下去,他把头埋在袖口破烂的胳膊弯里,静静地等着。估计下班急着赶着回家的人都走完了,现在过路的人应该是从家里出来遛弯的吧!张老汉心里想,下班的人走路都急匆匆的,脚步里透露着某种迫切的焦急。忙碌了一天,回到家里,人才算是真正地放松,从身体到精神,都可以真正地歇歇了。
张老汉是个农民,种了一辈子地,出尽了力,流尽了汗。他一直觉得农村人,天生的土命,土里刨食,日子过得辛苦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,就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。城里人,天生的金命,都衣着光鲜靓丽,生活惬意幸福。但现在,他突然有些可怜城里人,觉得城里人也挺不易的,陀螺一样,被日子挥舞得团团转!
遛弯的人走路都很随意,脚步里显着懒散,快一步走慢一步走都不会影响什么。张老汉还看见过一对年轻人,女的怀里抱着一只脑袋上扎满小、花辫的小狗,小狗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,穿着一套漂亮的花衣服。女人一边走,一边逗着怀里的小狗,很疼爱的样子。张老汉把头埋在胳膊弯里,不再用眼睛观察过往的行人,他只听脚步声,在脑海里判断着路过的人的人数、长相、出行的目的。买菜的一般都是下班回家的人,而且基本上都是女人。
这个季节,菠菜正是香嫩的时候,自家地里产的,张老汉也就卖的很便宜。回家的女人,都愿意买上一把两把的,回家煮面条,或者炒成一盘清香四溢的小菜。张老汉觉得有些累,也口渴得厉害。今年都七十三岁了,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叫自己走”,又在街上蹲了一天,不累才怪呢!
今天早上鸡打头鸣,张老汉就起了床。他站在院子里看看天,天黑糊糊的一片混沌,看不见一颗星星。天上的星星从啥时候开始看不见的,记不得了。张老汉小时候,总喜欢坐在柴垛上数星星,虽然从来就没有数清楚过。但那时天河灿烂,星光如水,天上的星星总是那么清亮,像一只只窥探人类的眼睛。听说星星是城里人先发现看不见的,现在,农村也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了。张老汉想,农村的星星从来就没有消失过,是自己老了,眼睛花了,星星还是以前那个星星,明明亮亮地挂在天上,只是自己老了。
张老汉从头门后边的钉子上拿了挂在上面的铲子,到门前的菜地里去起菠菜。春天习习的清风吹来,摇曳着菜叶上晶莹的露珠,露珠在熹微的晨光下,像一颗颗珍珠。张老汉感到有点凉意,用手摩挲了一下粗糙的脸颊。粗燥的皮肤相互之间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很快蔓延到了全身,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开始流动,张老汉觉得舒服了很多。他伸伸因衰老而变得僵硬的腰,蹲了下来,开始起菠菜。
年纪不饶人,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,天天都干活的张老汉觉得不知不觉地,腿也硬了,胳膊也硬了,手指的动作逐渐变得笨拙起来。做个大点的动作,都得先试探一下,唯怕一个不小心,把啥弄折了。张老汉一边感叹时光倏忽,转瞬就老迈了,一边一棵一棵小心地理顺菠菜的叶子,再一棵棵地擦着菠菜的根蔸起出来。他弄的很慢,很细心,像是在抚弄襁褓里年幼的儿子,怕弄疼了他们!
菠菜是去年冬天种的。从种子下地天就一直干旱,初冬没下一滴雨,一个冬天也吝啬地不肯落一朵雪花。菠菜的苗就稀稀拉拉出的不齐,出来的苗也不长,贴着地皮,寡黄寡黄的。以为就不行了,几次准备锄了种点别的,可是冬天也没啥能种,就一直那样放着,准备过了年开了春再说。没想到刚一立春,天就下了一场透彻的春雨,菠菜那瘦弱的身子骨好像得到了什么号令,一下子就挺直了腰身,齐刷刷直向上冲。今天去看一个样,明天再去看,又是一个样。一地的菠菜把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力量,可着劲地迸发了出来,转眼,就绿油油地长成了一大片。
这一片菠菜,又是一点新的希望。对张老汉来说,出力不怕,辛苦不怕,怕就怕没有希望。绿油油的菠菜一棵棵地起出来,用去年秋天就留好的玉米壳子扎成一捆一捆,再细细地洒上一瓢井水。洒井水并不是为了增重,张老汉不会用称,卖菜只会按捆卖。洒水是为了菠菜的新鲜度多保留一些时间,好卖些。
菠菜被一捆一捆整齐地码放在自行车上的两个竹筐里。自行车是一辆老旧的永久加重自行车,现在都很少见了,老张汉的自行车常年架着两个竹筐,很少取下来过。这辆自行车,可帮了张老汉不少忙。
卖菜的镇子不远,现在的路也修得好了,可老老汉带上两筐菜,骑自行车过去也不容易。张老汉觉得自己确实是老了,以前也常去镇上,骑上自行车,觉得那就不是个事儿。现在去一趟镇上,要用上以前两倍的时间,有时还更多。镇里有很多吃公家饭的人,不种菜,只买菜吃,都穿的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,手脚也瓷白瓷白的,干净爽气,不沾一星半点土星。
儿子满娃和儿媳妇秀娟也是公务员,可他们都在省城上班。张老汉想起了儿子和儿媳妇,还有孙子闹闹。闹闹都六岁了,他只见过三几回,儿媳秀娟嫌张老汉一口土腔土调,怕孙子跟着学,不喜欢张老汉和孙子在一起。其实秀娟也都好几年没回过家了。
儿子满娃倒是年年都回来一回,都急匆匆的,说工作忙得很,最多呆一天就走。回来主要是看看爹有没有存下点钱,有了就拿走,没了也不说啥,就走了。儿子一家都住在省城,离老家虽然也就百把十里路,但儿子说工作忙,平时不得回来。他知道,儿子在省城的房子要还房贷,那是一笔大钱,还有孙子闹闹在城里上学,听说现在城里一个娃娃上学,要补这课补那课的,学费动辄就是几千上万的,儿子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。
张老心里明镜儿似的,儿子嫌弃他呢!
张老汉想,得亏自己在农村生活,没啥成本,日子再紧巴,只要有一口饭吃,日子总能过下去。自从老伴走了后,他靠种地打零工,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,却无力为儿子在省城买一套房。张老汉怎么也想不明白,省城的房子怎么那么贵呢?听说屁股那么大一小块就得一万多块钱,那一百多平方得多少钱啊?张老汉无法想象这种天文数字的钱怎么能挣得到,只知道自己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,想像力实在是太贫乏了。像一只踯躅而行的蚂蚁,抬头看蓝天,就觉得渺远得不可想象,蓝天以外的宇宙呢,就更甭说了。本来,张老汉以为把儿子养大,成家立业了,自己就能歇口气了,现在看来,儿子就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无底洞,这辈子是没希望填满了。
把自行车收拾利索,张老汉回头看看路口树顶上渐渐明亮起来的天光,叹了一口气,满头花白的头发也跟着叹了一口气。得吃口饭吧!这一去就得一整天,现在街上的饭越来越贵了,吃一碗面,半筐菠菜就得白卖了。
张老汉走进大门,思谋着吃饭的事情。一个人的日子,吃饭常常胡对付,厨房对独居十多年的张老汉来说,有点多余,除了每月按时蒸一回馒头,他很少在厨房升火做饭。常常啃个馒头就算一餐了,想想凌乱的厨房,积满灰尘的碗碟,他连进厨房的心思都没有。进去了也是锅冰灶冷,没啥可吃的。
张老汉又想起走了的老伴。记得老伴胖胖的,天生一张笑脸,面团似的,常笑眯眯地。性子也绵,就没听见过她大声说话,一个多么和气的人啊!老伴在时,那时他们都很年轻,老伴总是把简陋的屋子收拾的很温暖,很整洁。那时的厨房里虽然也没有啥好吃的东西,但总是清清爽爽,干净利落。干一天活,累了,回到家里,院子里石凳上的洗脸盆里,早就备好了温热的水,浸着条热乎乎的毛巾。洗脸洗手,走进厨房,是他一天中觉得最幸福的时刻,饭菜肯定都准备好了。有时是糊汤就萝卜菜,有时是糁子就腌蒜苔,再吃上个热乎乎的玉米面饼,那被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身体里抽走的精气神,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身体里。那些日子多好啊!张老汉瞅了眼院子里的石凳,那个石凳还在那里寂寂地呆着,上面的尘土却厚得能抠下一整片来。张老汉的眼睛里有了潮湿的感觉,他揉了揉眼睛,把那种感伤的感觉揉进了身体,伤感就淡了,轻了。就是啊,老伴的声音、眉眼,他都有些想不起来了,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。时间过的真快,一晃,她都走了二十多年了。
张老汉轻叹了一声,那头雪一样乱糟糟的白发应声,也跟着轻叹了一声。他顺着坑洼不平的房檐台走到里屋里去。前几天蒸的馍头,怕老鼠咬,放在门后柜子顶上的笼子里。他取出两个馒头,坐在炕沿边吃了一个。热水瓶里的水不知道是哪一天灌的,还有一点微弱的温度,他把一只纯净水瓶子里倒满,盖好盖子。想了想,又拿起热水瓶,轻轻摇了摇,觉得还有些水,就往旁边的碗里倒。热水瓶里的水不多了,只倒了小半碗。他端起碗,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亮,看了看水面漂浮着的一层白色的面粉一样的东西。心想,现在的水,烧开了总会浮一层白色的东西。村里人说,自从村旁建了那座水泥厂,水的味道就开始变了,不像以前那么甘甜了。但张老汉觉得,不知道从哪一天,农民也开始变了,种啥都离不了农药,家家门房里都像在电影里看过的实验室,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药瓶瓶。农药是土地的鸦片,农药用多了,土地就上瘾了,就离不开农药了,哪一年不用农药,土地就犯瘾,啥东西也种不出来,得叫你一年白忙,颗粒无收。
张老汉摇摇头,决定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。他觉得自己老了,像快没油了的煤油灯,自家儿子的事情他都解决不了,什么工厂啊农药啊这些事儿,他一个农村的老头子又有什么办法呢!儿子儿媳一年到头不肯回家,他知道他们的心思。儿子儿媳嫌弃他是个农民,不是个有钱的大老板或者当官的,既没办法为他们谋个一官半职,也没办法帮他们在省城买一套房子,害他们背着这么沉重的房贷,得背三十年呢!儿子多辛苦啊,他有些心疼儿子,觉得儿子儿媳妇也可怜,也为自己不是个大老板而觉得对不起儿子。他想,得赶紧去卖那两筐菠菜,卖多少算多少,多多少少对儿子总是个帮衬。自己老了,能将就,儿子儿媳还年轻,总得过几天舒心日子吧!还有那个虎头虎脑,叫人心疼的孙子闹闹。
村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,村里现在只剩下一些老年人了。有些老人一个人住的时间长了,就会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,就是自己和自己讲话解闷儿。村东头的李婶就这样,她常常大声和自己说话,说着说着,就忘了是跟自己说话,把自己吓一跳。隔李婶家不远的留着长胡子的本家大哥张老胡,也常常自言自语,和自己说东说西,满世界乱扯。张老汉却没有这个习惯。他一个人呆着时,最多是想想各种各样的事情,从来不会一个人讲话。
他从炕头的枕头下找了个布袋子,把装了水的纯净水瓶子和两个馒头装进去,锁好头门,到镇上去卖菜。太阳还没有出来,但天已经亮光了,村庄的空气凉飕飕地,一吸一呼,很舒坦。自行车都骑了十几二十年了,还是年轻结婚的时候买的,修了又修,锈迹斑驳,沧桑的像个老头子。张老汉骑习惯了,觉得加重自行车骑上稳当,心里踏实,带上两个装满菠菜的竹筐,稳妥妥地,纹丝不动。到镇上时,太阳还是没有出来,看样子今天是个阴天,但天上亮堂堂的,看不出云的影子。
张老汉驾轻就熟地找到了街转角的那棵苦楝树,他时不时地抽闲出来卖些地里产的物产,常常就在这棵树下。卖的东西有时是一小筐杏,有时是几捆小葱,有时是十几个嫩玉米棒子,只要能换成钱的东西,他总舍不得自己吃,想着拿出来换成零钱。他怕看儿子回来拿钱时,看到那几张可怜的钞票时一声不响,没有一点表情的脸。
张老汉在树下铺上一张塑料纸,把菠菜一把一把地摆上去。菠菜经了一路的颠簸,还是精神抖擞,鲜绿翠亮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摆完筐里的菠菜,张老汉往后退了两步,看了看摆好的菜摊子,整整齐齐,像一座小山似的。他对自己无声地笑了笑,他很满意今天菠菜的表现,争脸呐!
清早出来买菜的都是一些老太太。第一个走近摊位的老太太一头白发,戴着副黑框眼镜,看起来很慈和,话也多,菜买的很细发,翻过来翻地去地看了很多遍。菠菜一把一块钱,走到跟前问多钱一把,翻一会儿再问多钱一把,再翻一会儿又问多钱一把。张老汉都耐心地解说回答,人老了,忘事快。他庆幸自己还能耳聪目明,心里清楚,要不然,咋办呢?老太太又说菜有点老,不鲜嫩。张老汉知道,菠菜用化肥种,只要水跟上,就长的又快又大,看着嫩绿鲜亮,但那是菠菜吗?吃起来滋味寡淡,没有一点菠菜的香味儿。自己的菠菜施的是农家肥,去年冬天又干旱,所以长的就慢,看起来老相些,但这种菜积攒的养分多,吃起来更香,有甜味儿。张老汉不会用绿色蔬菜这样的名词解释,觉得骗人似的。
最后,老太太还是买走了两把菠菜。走时还问:“你明天还来这儿卖菜吗?”张老汉觉得自己有些重要,就郑重地对老太太说:“来,铁定来,地里的菜还有一大片,得卖一段时间呢!”说完,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轻松和愉快,明天,老太太肯定还能来买自己的菜。
老太太买了菜了后,就算开张了。陆陆续续地,不断地有顾客光顾。有的老太太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的,懂货!拿起一把菠菜看了看,问下价钱,见卖的也便宜,二话不说,就给自己的提兜里塞,一塞就是六七把。有的老太太也墨墨迹迹、磨磨蹭蹭地,挑三捡四,嫌东嫌西,说一大堆弹嫌话,但最后也会买上一把两把的菜。张老汉不管碰着什么样的老太太,都一律笑脸相迎,俗话说:弹嫌的才是买主。他能解释就解释两句,有的老太太太说话刁钻,没法解释,他就笑着一脸和气,不说话。
张老汉常来卖东西,知道怎么样才能多卖点。一大堆菜,一大早卖就卖出了多半,中午就一直没人来买菜。张老汉抬头瞅瞅天,没有太阳,天光却亮得逼人的眼,树的叶子浓绿,偶有一点罅隙,透下来的光亮如果正对了眼睛,就能让人睁不开眼来。这棵苦楝树是镇上搞绿化时栽的,张老汉年轻时这棵树只有胳膊粗,张老汉老了,树也在不知不觉中蓬勃成了一棵参天大树。张老汉想,不知道这树是从哪儿弄来的,在农村咋没见过呢?张老汉很满意自己找的这个地方,如果天下雨,在树下蹲着,也不会淋上雨。
张老汉整理了一下菜摊,把顾客扒拉菜捆时掉下来的菜叶子捡起来,整成一把,放进竹筐里。这些菜叶子带回家,吃饭时用开水焯一下,撒上一撮盐末,味道就好得很。做完这些,张老汉见一直没有顾客再光顾菜摊,觉得有些无聊,就靠着大树,圪蹴下来,一会儿就眯了眼睛,打起盹来。
天光开始暗淡下来的时候,街上下班的人开始多了起来,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,还有一些中年人,脚步都急急的。有的老远就睬见了他的菜摊子了,径直地走过来,掂起两把菜,问:“多钱一把?”他回答了,来人就丢下两块钱的零钞来,不再说话,拎着菠菜,又急匆匆地走了。有的骑着电动车,车头把一歪,在他菜摊前停下来,用干净的皮鞋点着地,不下车,喊:“老汉叔,装两把菜。”他就赶紧装好菜递过去。有一个披着一头长头发,面容姣好的妇女,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叩着清脆的音节,都从他的菜摊了走过去了,又“嗒、嗒、嗒”清脆地返回来,买他的菠菜。她好象一直在想着别的事情,都走过去了,才想起来晚上做饭,还得买把菜。
陆陆续续,总有人来买菜,让张老汉一阵忙,他的额角微微出了汗。汗湿湿地顺着额头上的皱纹向下蠕蠕地渗着,痒痒的感觉的就在脸上蔓延了开来。张老汉抽空用手背擦了一把,痒痒的感觉就消失了。他看着菜摊上的菜在不断地减少,一些轻松愉快的感觉,再次从张老汉的心里升腾起来。再坚持一会儿,也许就卖完了呢!
人流终于稀少下来了,买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终于,最后三把菠菜在摊位上蔫巴巴地躺了快一个小时了吧,就是不见一个人走近。张老汉抬头看看夜色暗合的天空,树影都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了。下午一直在树叶间激烈地商量什么事情的两只麻雀,可能也歇着了,听不见声息。
张老汉有些泄气了。在大树下蹲了一天了,中午啃的那个干馒头,好像一片雪花融化在水里一样,轻飘飘地,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饥饿的感觉隐隐约约,若有若无,像一个从远处走过来的一个熟人,好像认识,却始终看不清到底是谁,是得饿了。一整天就吃了块馒头,那一瓶水啥时喝完的,他都记不清了。张老汉有些懊恼,早晨出来时,就该多带块馒头,水又不要钱,也应该多带点才对呀!
张老汉有点想收摊,但看了看剩下的那三把菠菜,就是下不了决心。三把菜,卖了就是三块钱,就能给儿子多添一点劲。虽然,三块钱对省城的一套房来说,连九牛之一毛都算不上,但他真的想孙子了。孙子长那么大了,该上小学了吧?但他只见过三两回,小家伙长得快,现在,孙子闹闹的样子他都越来越模糊了。上一回见,还是闹闹三岁多时的样子,那小模样,多让人心疼啊!如果儿子,儿媳心情能好一点,愿意把孙子带回来,在家里呆一天,那怕半天也行,让他和孙子在一起玩上那么一会儿,那得多让人高兴啊!但他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儿子一年回来一回,也只是象征性的,因为他每次都让儿子失望,儿子也对他不报什么希望。他想,有啥办法呢?农民挣几个钱太不容易了。
张老汉决定再忍一忍,再坚持一会儿,说不定,就真就有回家时忘了买菜的人,回头再把这三把菠菜给买了呢!街上的路灯开了,朦朦胧胧地,天反好像突然就黑下来了。路灯的光照着树影,影影倬倬的,树下的光线就更暗淡了。张老汉想,过路的人能看见卖菜的摊子吗?得再给路边上挪挪,挪到路边,路灯能照着的地方,过路的人就能看见了。但他浑身的力气匮乏的厉害,一动也不想动了。于是就静静地在树的暗影里坐着,头埋进胳膊弯里,只留两只耳朵在外面,接收着周围的声息。
“爸爸,你看那个老爷爷睡着了!”张老汉觉得那声音好像来自很遥远的远方,跟自己丝毫也不相干,就动也没有动。“爷爷,你怎么在这儿睡觉了?”这次,张老汉听明白了,在叫自己吧?一抬头,看见身边站着个两个人,树影暗暗地打在他们的脸上,看不太清白。一个小男孩,五六岁吧!该和孙子闹闹差不多大小了,牵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却和儿子满儿一点都不像,儿子从小跟着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,长得跟黄豆芽儿似的,瘦弱弱地,书却念得好。长大后,个头倒不矮,却还是瘦,从一颗黄豆芽变成了一根细细的竹竿,一根倔强的竹竿,一点都不像眼前这个年轻人那么魁梧的身体。
小男孩回身拉着年轻人的胳膊,使劲地摇着,眼睛却一直盯着张老汉看。张老汉的表情就有些不自然,心里的懊恼感觉又升了起来:唉,到底扛不住老,这么一小会儿,就睡着了!
年轻人低下头,关切的声音:“老汉叔,卖菜呢吧?这么晚了,该回家了。”一边转头瞅着摊位上那三把蔫头耷拉的菠菜。菠菜在暗暗的树影下,黑糊糊的,连仅有的那点儿绿色也看不出来了。张老汉嘴动了动,却说不出话来。
年轻人蹲下来,说:“这几把菜我要了,你得回家了。”他低下头,自己把那三把菜装了起来,从口袋掏出一张二十块钱钞票塞到老汉手中,张老汉呆呆地看着年轻人,忘了还得找钱给年轻人。年轻人手脚不停,又帮张老汉收拾菜摊子。张老汉看了看小伙子的脸,觉得,小伙子的眼睛,还是和儿子有点像。
“爷爷,这袋饼干给你吃吧!”张老汉才注意到,小男孩手里,还举着一袋饼干。饼干袋被他的小手高高地举起来,眼睛里透着热切。
张老汉的眼睛湿润了。

 老斯基加油站
老斯基加油站 渠村的春天
渠村的春天 大风之夜
大风之夜 多想再观赏一次这盛世美颜!
多想再观赏一次这盛世美颜! 返校
返校 冬天
冬天 书签
书签 骆驼祥子观后感
骆驼祥子观后感 奇女花木兰
奇女花木兰 勤则不匮 劳则充盈
勤则不匮 劳则充盈 其实自信一些,唱的也不见得多差。
其实自信一些,唱的也不见得多差。 沉淀
沉淀 故乡红枣
故乡红枣